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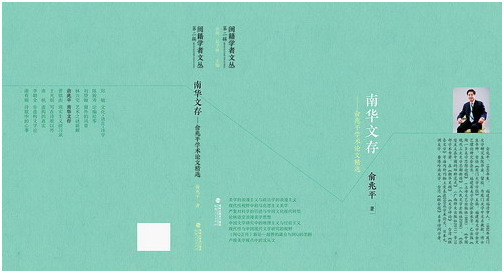
近日,厦门大学教授、著名学者俞兆平出版了《南华文存——俞兆平学术论文精选》一书,该书是这套《闽籍学者文丛》的新书。
作为一位在美学、文艺理论等方面著述丰富、建树颇高的学者,俞兆平不仅对鲁迅笔下的人物、闻一多的美学思想、闽籍诸位学问大家的学术理论等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解析,对韩剧流行、追星族、国内影视剧本创作同质化等文化现象和问题也有一针见血的看法和评判。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妙语连珠,讲述闽籍“大腕”学者严复、林语堂等治学趣闻,并对时下热映的《悟空传》等《西游记》名著改编,也有精妙的评论。
>>俞兆平荐书
我从事的专业是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既侧重于文论,自然就不能局限于文学的范围,哲学、美学的书籍也是时时关注的。
若论对我影响深刻的著作,是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及其“三大思想史论”,那是20世纪80年代,禁区初开,饥渴的灵魂碰触到的第一口甘泉,从而奠立了我以德国古典哲学、美学为根基的理论体系。
退休后,阅读的书籍多散漫无羁,最近印象较好的书是毕飞宇的《小说课》,作家型的批评家对名作精到的剖析会让高校文学教授失业;还有是夏中义的《百年旧诗 人文血脉》,填补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关于旧诗类别的叙述空白;还有约翰•格里宾的《寻找薛定谔的猫》,为我们拓展出与牛顿经典物理学完全不同的量子物理学的世界,是对人类传统的认知方式的挑战。
>>作家名片
俞兆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后留校任教、任职,从事美学、文艺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已出版《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写实与浪漫》《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等多部学术专著。
谈闽籍大家
外表严肃的严复
其实幽默风趣
问:您在《南华文存》第二辑“闽籍文人评鉴”中,点评了严复、林语堂、林庚、郭风、蔡其矫、孙绍振等六位大家,他们的哪些特质吸引了您的注意?
答:身处闽地,自然对家乡的人文名家有所关注,但要说是着意选择,怕是没有。至编辑《南华文存》整理旧文时,才从中选了以上六大家。
我感兴趣的是各位名家的一些活生生的个体感性特质,像严复,一提到他的名字,你们眼前一定会闪现出一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老爷子的形象,其实老爷子有时也挺好玩的。他讲逻辑学的归纳与演绎概念时举二例:有一小儿,原不知火,手初触被烫,足再触又烫,于是得出“火能烫人”之“公例”,即从个别综合、归纳,得出一般,亦称之“内籀”,此为归纳法。而他对演绎法则有些嫌弃,认为它不过是从已知的一般“公例”推导至个别、特殊,亦称之为“外籀”,但此法不过是将古人已经得到的道理,如一桶水倒向另一个桶中,倒来倒去,总是这水,难以产生新知识。艰深的学理经他这么一比说,立即显明,深入浅出矣。
学界曾有一媚俗之气,一讲到鲁迅、林语堂在厦门,就是前者与许广平,后者与廖翠凤、陈锦端的恋情,好像厦门的风气特别容易逗引名家们谈情说爱似的。其实厦门时期也是鲁迅哲学思想转换的萌始之点,擅长写幽默小品文的林语堂也有对深奥美学理论的追寻。林语堂最重要的两本理论著作是《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啼笑皆非》。近现代西方美学所津津乐道的“物化”或“物质主义”的问题,早在中国儒家典籍中就已论及。而在中国现当代美学研究界,林语堂可能是解读、揭示出这一概念所具有的重大美学意义的第一人。
再说说孙绍振。收入“闽籍文人评鉴”的是揭他“老底”的文章——《孙绍振诗学体系的哲学底蕴》,我发现他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四次引述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在文章最后做出判断:这位 “孙大圣”,并非什么离经叛道的异类,而是骨子里浸透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理论的一位人物,他的理论体系仍属于古典美学的范畴。由此,也就容易理解到,最近他何以对那些建立在后现代哲学基础上的西方文论,基本上持批判态度。
谈名著解读
客观存在文化现象
不能轻率否定
问:当前有一股名著解读风,对文学名著进行各种所谓现代视角的解读,其中不乏牵强附会或戏说笑谈,您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多年,怎样看待这样的风气?
答:我注意到这股“名著戏说”风潮,它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自周星驰《大话西游》问世,此风开始盛行,其实魏明伦的《潘金莲》早开先河,对之需具体辨析。若先剔除出恶搞、胡搞的一类,像今何在的《悟空传》、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确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艺术传达形式,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接受群体,有些粉丝甚至把《悟空传》中的台词:“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作为座右铭。因此,不能轻率地予以否定。
若追索这一风潮的动因,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哲学上世界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经典的轻慢,对神圣的拆解,对价值的新见等,是诱发的最根本原因;二是科技的发展,数字网络为年轻一代拓展出另一神奇而虚幻的世界,一切真实都可重构,一切欲望都可尝试,一切念想都可诉求,他们便借名著为外壳,借其中人物为符号,别开生面,另创新地了;三是其后市场的介入,当它发现其中有利润空间可图时,便推波助澜了,如以金陵十二钗来命名房地产,则带有挑逗意味。
“名著戏说”比较集中于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其中《西游记》被“调戏”得最多,不仅中国人“戏”,老外也“戏”之。日本、韩国的唐僧是女的,而且会法术;越南的悟空是童星;德国改师徒取经为观音寻书;美国则让悟空和观音谈恋爱……中国的各种版本更是数不胜数。何以如此呢?一位外国评论家有如下之说,因《西游记》是神话传说,是魔幻小说,超越现实,适合网络,再创造的余地与空间较大。其实创作者均是借他人之杯酒,浇胸中之块垒,以名著某一原型、某一节点、某一伏笔等,为触发之点,为伸引之梗,在再创作中吐露、倾诉自己的价值追求、人生欲念、审美情趣等。
至于为民众所诟病的“戏说”,则是那些恶搞、胡搞,他们对古典名著随心曲解、恶意解构、胡乱编排、肆意戏谑,如此不尊重当然换来的是摒弃。而经时光与历史淘洗而积淀下来的名著、经典,则已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化价值与文学典型形象,经受得起各种风潮的侵袭,不必过于担心。那些无聊的折腾,我倒觉得有点像20世纪60年代的“打鸡血”之风一样,很快就会沦为笑柄。
(本报记者 杜晓蕾)


